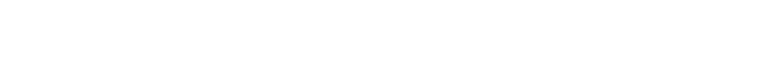如果关于普遍基本收入(UBI)的公开辩论要从世界各地发生的许多UBI实验中受益,那么参与辩论的记者、决策者和公民需要了解UBI实验可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做什么。UBI的实验可以让我们对UBI的一些影响增加了解,但它们似乎并不能达到许多记者、公民和决策者所期望的效果。2016年12月份,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完美地解释了普遍的对UBI的过分期望,标题刊登为:“2017年,我们将明确基本收入是否有意义”。尽管我们想通过UBI试验明确测试出其功效,但试验并不能得出某种决定性的信息,来影响绝大多数人支持或反对UBI的决策。
社会科学实验并不像医学实验。例如,一次疫苗试验,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几乎每个人根本关切的问题:疫苗是否安全并行之有效?研究者可以通过选择试验对象群体(1000个人接种疫苗,对照组1000个人接种对照剂)进行随机对照试验(RCT)。他们观察两个群体来确定实验组感染疾病的几率是否更低,是否更容易出现并发症。疫苗实验并不是完美的试验。随机对照试验在确定疫苗在长期范围内对于各年龄段的人群,和对于有复杂风险因素的人群是否安全有效上有一定困难,但一次随机对照试验报告的对照组和试验组的区别给人们提供了他们所关切的根本问题的有用并相对直接的信息。如果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比较表明一种疫苗既安全又有效,人们就应该使用它,如果比较说明疫苗不安全或者有效性低,人们就不会使用。如果有明确理由证明试验结果不可靠,那么研究者应该进行更多的试验。
我们可以对实验组进行一段时间的UBI试验并且和对照组比较他们的行为和生活结果。但是这种比较并不像疫苗试验那样,就是完完全全对UBI的试验。如果UBI试验并算不上试验,那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间接性的,并且总是带有不确定性的方法,提升我们对于UBI的特定方面而不是其他方面的了解。UBI试验不是像疫苗试验那样具有决定性。UBI试验不可能像疫苗试验那样具有决定性,因为它们对全面实施的国家UBI计划的长期效果的评价要远远低于疫苗试验对全面实施的国家疫苗计划的长期效果的评价,而且因为即便RCT结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关于一个全国性的UBI项目的某种有意义的信息,伦理上的分歧也会影响我们对其效果的评估。
不像疫苗那样,UBI有许多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和国家市场以及非市场环境中人们彼此交流的方式。随机选择的一个工人接受UBI,其行为上的变化可能与1亿接受UBI工人的变化很不相同。雇主对于这两者的反应变化也非常不同。实验性UBI对一个随机选择的三年制UBI中的一个五岁儿童的教育效果可能与在一个国家中对500万五岁儿童全面实施UBI的教育效果大不相同,因为UBI将在他们的整个学校生涯中发挥作用。
我们想对UBI了解的事情相较于疫苗来说,要复杂且难以观察得多。一旦受益人和其他人对UBI和其他人的反应与他们的行为互动,UBI会给他们的收入增加多少?而这又会给受益人增加多少福利?根据什么样的福利衡量标准?受益人对UBI反应使其更加昂贵吗?还是以政策制定者想要的或是不想要的方式作出反应?这些因素在评定UBI中的相对伦理重要性又如何计算?
伦理上的分歧会影响我们对于几乎所有UBI效果的评价。例如,如果实验组相比于对照组工作更少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这使处于不利条件的人去追求更好的薪资,去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去追求更好的教育,或者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或者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使他们违反一些原则:并不富有的人一定要尽可能多的工作?经验主义的结论总是易于歪曲和滥用,如果人们使用它们不是为了帮助完善思想而是作为支持他们对于此类问题固有观念的武器。
UBI试验会对部分效应产生更好或者更量化的信息。这一无关紧要的事实使得实验容易受到街灯效应的影响,从而引起人们对更容易回答但不太重要的问题的关注,而忽视了更难回答但更重要的问题。例如,与那些在食物、住房和其他经济不安全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相比,那些成长在因为国家UBI而永远不会面临食物或住房不安全家庭的新生儿童是否倾向于成长为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幸福、更有生产力和更亲社会的成年人。
RCT 可以回答对照组是否比实验组工作时间更长的问题,但他们无法回答雇主是否会通过提供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来响应全国 UBI,以及这些工作场所的改善是否会部分扭转最初的在劳动时间方面的下降趋势。像一个明灯,UBI 实验将把每个人的注意力——即使是最理性、最有见识的研究人员——吸引到通过对照组和实验组之间的比较产生的可量化数字上,远离更重要但难以回答的问题。
出现这样的情况,部分是因为 UBI 影响的复杂性,部分是因为伦理上的分歧,UBI 不适合用类似于疫苗是否安全有效的简单的底线问题去决策。在医学意义上,UBI既安全又有效。 UBI 将提高净受益人的收入,而无需让他们承担任何工作义务或证明他们有需要,并且不会使他们患上荨麻疹或出现任何其他医疗并发症。关于 UBI 的主要分歧不在于未知数,而在于其众所周知的影响的伦理价值:无论低收入人群是否工作,政府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的政策是对还是错?人们根据他们对这个道德问题的回答,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下定决心(做决策)都是合理的。
UBI 是否可以显著提高净受益人的收入(无论他们是否工作)这一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实证调查,因为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其能,且几乎没有异议;分歧在于是否应该这样做。对 UBI 影响的实证研究几乎无法解决基本的道德分歧。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X 美元的 UBI 是否可持续,但对于 X 的大多数相关水平,这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并且答案只会对支持 X 美元 UBI 的人群具有决定性。 UBI 的反对者和怀疑者基本上并不是因为认为提议的水平是不可持续的,否则政治辩论中的人都会是UBI的支持者,只是对金额的高低有分歧而已。
上述问题使研究人员无法制定类似于疫苗是否安全有效的底线问题,也无法对具有不同道德立场的人感兴趣的任何底线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所涉及的许多权衡的伦理评估,甚至是某些影响是否应该被视为积极或消极的问题,都在旁观者关注的范畴内。
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还要进行 UBI 实验呢?人们进行 UBI 实验的部分原因是出于战略政治原因,因为即使存在所有这些困难,更多的知识总比更少的好。并不是每个人都对 UBI 有强烈的看法,而有强烈看法的理性人仍然愿意根据新知识改变他们对 UBI 或某些方面的看法。
但信息不是知识。只有当人们理解它及其相关性时,更多的信息才能产生更好的知识。进行实验的研究人员没有能力消除上述讨论的所有潜在误解。研究人员接受过进行实验并将他们的发现报告给其他专家的培训。就研究人员向非专业人士展示他们的发现而言,通常是为了帮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研究。
这就是随机控制实验,这是一个对照组;这是一个实验组;这些是控制组和实验组之间的测量差异。研究人员添加一堆关于这种比较的有限相关性的警告会令外行呆住。随着警告越来越长,记者、政策制定者和公民更有可能直接跳到数字上。对这些警告的充分理解可能会让人们对实验结果表明完全实施的长期全国性UBI 计划的实际市场影响如此之少感到失望。
研究人员可以将他们的实验结果与其他来源的证据结合起来,并使用模拟模型等工具将对照组和实验组之间的差异转化为对实际市场结果的估计。他们可以将这些结果与更多数据和模型结合起来,将市场结果的估计与具有不同道德立场的人关切的各种底线问题的估计答案联系起来。但这将涉及在 UBI 实验之外进行更多的非实验性研究。他们的结果将更多地由这些模型的假设和其他证据来源驱动,而不是由他们正在报告的实验的实际发现驱动。
我最近的书《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公民基本收入实验的批判性分析》探讨了进行和报告 UBI 实验结果的难度,以通过UBI实验帮助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公民尽可能多地获得有用的知识。 [3] 本文试图总结该书中的一些最重要的论点。
这本书讨论了几乎任何UBI实验都必须处理的几个一般性问题:社区效应、长期效应、观察者效应、路灯效应、分离所研究项目的大小和类型的影响的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测试真正的UBI的不可行性,以及使用收入状况审查项目作为UBI的实验近似所产生的问题。[4]
尽管这本书没有在人们是否应该进行UBI实验问题上表明立场,但它讨论了进行实验的科学和战略原因,以及过去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的实验记录。几乎所有的实验都成功地收集到了有用的信息。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成功地加深公众对UBI的了解。例如,上世纪70年代进行的实验被严重误解,他们的发现经常被有意或无意地用来误导公众。[5]从UBI支持者的角度来看,一些实验在推进UBI运动方面取得了战略成功,而另一些则没有。可以说,上世纪70年代的实验对当时的UBI运动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在今天产生了积极影响。大约10年前在纳米比亚和印度进行的实验似乎对推行世界范围的UBI运动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最近实验的效果还有待观察。[6]
本书的目的不是批评当代的实验,而是为委托、设计、施行、报道和阅读的人提供一些有用的分析。为了从实验中得到最大的收获,所有人都需要知道,在相关的政治背景下,讨论UBI效应的哪些问题是重要的,哪些问题是由实验回答的,最重要的是,实验结果表明了什么和没表明了什么。作为实验的实施者和报道者,研究人员和记者需要了解他们的发现是如何被误解和误用的,从而让实验发现在当今的争论中变得有意义。[7]
这本书讨论了令人惊讶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学,它引发的UBI实验更多是对希望立即引入UBI的运动的反应,而不是对UBI进行尝试的反应。对于UBI运动来说,UBI实验是一个有风险的策略,但只要UBI仍然是一个政治上的高风险项目,实验就有可能缩短它的进程。
任何人在决定进行UBI实验之前都应该意识到事物的内在复杂性以及相关人员背景知识的差异。 因此,他们也应该意识到,实验结果容易被误解和误用,他们需要制定战略,尽可能增加理解,减少误用。
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这本书能做的就是尝试提出这样的战略方法。我们可以按照如下方法操作。把实验看作是回答评估UBI作为政策议程所需问题的一小部分努力。仅用自己的术语和一些限制警告来解释实验是不够的(什么是随机对照试验;什么是对照组;什么是实验组等)。实验不必与其他研究工作一起进行,以回答有关UBI的所有问题,但单独进行的实验对UBI作为一项政策所能提供的信息极其有限。实验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对这一更大努力的微小贡献。为了让非专业人士理解这一点,需要有人帮助他们理解实验方法的局限性,以及将实验结果与他们真正想知道的关于全面实施的UBI计划的事情联系起来所需的额外证据。[9]
除去其他的更具体的建议,该书还强调了四种广泛的策略,以帮助实验启发关于UBI的讨论。
1.从公开讨论到落地实践到继续前进的追溯工作。任何委托、进行或撰写实验的人都应该尊重关于UBI的国家或地区性讨论。找出人们最想知道的事情。设计一项研究,尽可能地针对那些对讨论很重要的问题,着重关注实验是否能够提供相关证据的程度,以及非实验数据和模型可以提供帮助的程度。[10]
2.关注UBI的主要影响而不是副作用。街灯效应使得过去的实验更加关注可量化的副作用上,比如以牺牲更重要但更难以量化的问题为代价去关注劳动力和成本,而忽视了UBI是否对支持者们预测的人民长期福祉有积极影响。[11]
3.关注底线。尽管公众讨论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差异很大,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任何一个底线,但对问题答案的渴望是无处不在的。因此,实验报告必须说明具有不同伦理立场的人们如何利用研究结果对UBI作为一项长期的国家政策进行全面评估。实验本身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回答一个底线问题,但研究人员可以将他们的所有发现与之联系起来。公民和政策制定者通常需要大量的帮助才能有意义地理解这种关系。[12]
4.解决伦理争议。研究人员无法解决关于UBI伦理评估的争议,他们也不应该尝试解决。但倘若他们忽视了这一点,反而对公众造成伤害。他们可以通过认识到这些争议,并解释这些发现对那些持有不同道德立场的人意味着什么来更好地避免混乱颠倒,这在当地和国际上经常出现。[13]
全面实施的全国UBI的总体成本效益可能是最接近底线的问题,与有关伦理分歧各方的人有关,但任何不同利益者关注的具体底线问题也是重要的。[14]这本书讨论了支持者和反对者提出的主张,并试图确定关于这些主张的可验证的实证问题。几个不应被忽视的经验主义主张无法在实验规模上进行检验。关于这些主张的证据必须来自其他来源,这些来源必须与实验证据相结合,将任何实验发现与任何相关的底线问题联系起来。[15]
虽然实验本身不能决定性地回答关于全国UBI的任何问题,但这本书确认了许多关于UBI实验可以部分检验、间接检验和/或非决定性检验的说法。它讨论了这些局限性对进行研究和交流其结果的影响。[16]这本书没有对UBI实验是否应该或不应该进行的问题采取立场。这个答案取决于当地政治环境的特殊性。问题不在于是否要做实验。现在全世界都在进行实验。问题是如何从他们身上学到最多的东西。[17]
本书最后讨论了如何在认识到这些主张在UBI讨论的政治经济学中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从实验结果走向公众讨论。因此,它们可以被解释为克服沟通障碍,减少误解和误用实验结果相关的问题。[18]
我希望我能说这个策略完全解决了问题,但那是不可能的。社会科学实验是一种非常有限的工具,其含义本身就很难理解。将实验作为回答所有关于UBI的重要实证问题的更广泛努力的一个小而不完整的部分,这种努力将会有所帮助,但不会消除误解。[19]
在如此复杂的问题和如此复杂的证据的讨论中,人们之间总是存在着理解的鸿沟。如果一个非专业人士学会了专业人士所知道的一切,他们就会成为专业人士。但实验和交流总是可以改进的。我希望这本书、这篇总结文章和这期特刊能对这种努力做出一点贡献。
[1]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draws heavily on the book, A Critical Analysis of Basic Income Experiments for Researchers, Policymakers, and Citizens, Karl Widerquist,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I summarized that book very differently in the article, “The Devil’s in the Caveats: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Difficulties of Basic Income Experiments,” Karl Widerquist, CESifo Forum 19 (3), September 2018, 30-35.
[2] Jamie Condliffe, “In 2017, We Will Find out If a Basic Income Makes Sense,” MIT Technology Review, December 19 2016.
[3] Widerquist,基本收入实验的批判性分析
[4] 威德奎斯特,⟪关于基本收入实验的批判性分析⟫ 第 19-42页.
[5] 卡尔 威德奎斯特,2005.“沟通的失败:我们能从负所得税实验中学到什么(如果有的话)“《社会经济学杂志》34(1):49–81;威德奎斯特,《基本收入实验的批判性分析》, 第43-56页.
[6]威德奎斯特,⟪关于基本收入实验的批判性分析⟫,第57-70页.
[7] 同上。 第77-92页.
[8] 同上。 第71-76页.
[9] 同上。 第11页.
[10]同上,第11页。
[11]同上,第12页。
[12]同上,第12页。
[13]同上,第12页。
[14]同上,第93-98页。
[15]同上,第99-114页。
[16]同上,第115-130页。
[17]同上,第141-144页。
[18]同上,第145-150页。
[19]同上,第12页。
Thank you to Chunzhuo Zhang (Joey), Fang Yuan (Sherry), Xianwen Huang (Amanda) and Qihao Liang (Qihao) for this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English can be found here.